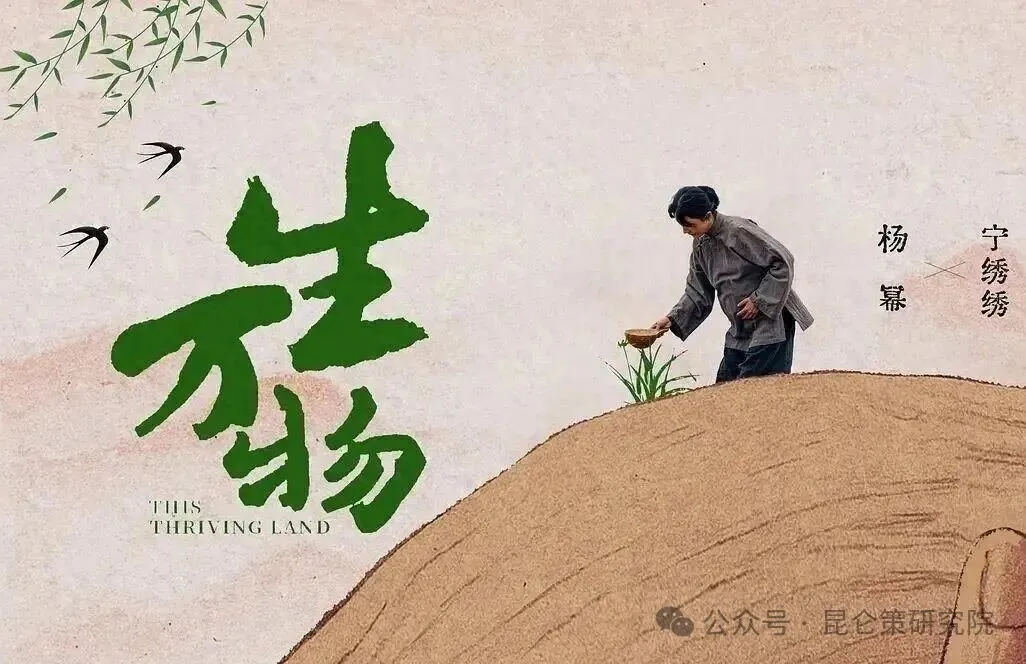
【作者按】2025年8月24日,看完了《生万物》36集,写下了这篇观后感。文章分上中下三集登出,这是文章的上集。
一、人性
《生万物》是一部反映20世纪上半叶,旧中国农村生活状态的电视剧,也是一部很有争议的电视剧。央视8频道首播结束后的第二天,导演刘家成就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创作谈:
——“没有真实,年代剧就没有意义。……观众之所以感觉人物形象鲜活,就是因为我们努力做到每个人物都有原型,不做扭曲化、脸谱化的艺术处理——真实的人物总是最有感染力的。”[注1]
刘导在《人民日报》发文,这是否意味着官媒的态度?不妄议。即便如此,也依然挡不住旗帜鲜明的分歧。
刘家成先生自信地说:“我将继续沿着突破自我的路走下去,坚持回归土地、回归人性,回归艺术本真”[注2]。人性是《生万物》的戏眼,也是观众分歧的焦点。我就从人性的分歧开始讨论。
右边的看官认为,《生万物》之所以可信,就在于它没有把旧中国的地主和农民脸谱化,而是真实地演绎了人性的多重性和复杂性。
左边的看官则认为,《生万物》所谓的真实,其实是用抽象的人性来遮蔽真实的社会关系,企图掩盖旧中国农民与地主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。如此而已。
实事求是地讲,对于右边的看法,不少人投了赞成票。一位朋友看了《生万物》后说:“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简单的好人或坏人,现实中的人既是天使又是恶魔。这就是真实的人性。”
不奇怪,右边的看官一定会给《生万物》的人性投赞成票。但我也注意到,投赞成票的,未必都是站在右边的人。
什么是“人性”(即“人的规定性”)?
刘少奇把人性概括为:“动物性和理性”。少奇同志的意思是说,人性是二重的,既有自然属性(动物性),又有社会属性(理性)。毛主席表示反对,由此引发了毛主席与刘少奇在人性上的分歧。
毛主席一再强调,人性就是“人的社会性”,他老人家说:
——“(人性)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——社会性,不应该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:一是动物性,一是社会性,这样说就不好了,就是二元论,实际就是唯心论。”[注3]
那么马克思怎么看待人性呢?马克思说: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这里说的“人的本质”,即人的根本规定性,也就是人性。所谓“社会关系”,通俗地说,就是人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联系,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地位。所谓“总和”,就是加总、合计的意思。
毛主席把人性概括为“只有一种特性——社会性”,完全符合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定性。人性的外在表现是多元的(所谓“既是天使又是恶魔”),但人性的根本规定却只能是一元的(即毛主席说的“社会性”)。
右边的看官说“人性是多重的和复杂的”——甚至也有不少左边的看官,也跟着这样说。这话并非全无道理。因为人们观察到的人性,总是呈现出“既是天使又是恶魔”的样态来。
然而,我说“并非全无道理”,也只是说“在现象层面有道理”。因为所谓“既是天使又是恶魔”,仅仅意味着人性的表现是多重和复杂的,却颠覆不了马克思对人性的定性。
很遗憾,《生万物》的编导和演员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听说过,这世界上居然还有什么“马克思主义人性论”?
作为主流电视剧,《生万物》闭口不谈唯物史观人性论,却大力宣扬唯心史观人性论。这在历史唯心主义盛行的今天,并不让我感到意外。
我好奇的是,究竟是因为不懂唯物史观,所以才被唯心史观忽悠了呢?还是因为“革命死了”之后,抽象的人性从此具有了时代的政治正确性呢?
二、阶级性
在阶级社会,人性归根到底就是人的“阶级性”。
按照马克思主义人性论,既然人性是人的“社会性”,那么,阶级社会的“社会性”就是“阶级性”。正如毛主席所说:“在阶级社会中,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,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。”
把人性的外在表现(“既是天使又是恶魔”)当做人的根本规定性,将人性与人的阶级属性划清界限,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从此人间蒸发——这并非《生万物》的首创,也不是充斥影视的各类神剧的专利,而是唯心史观人性论的根本逻辑。
悲催的是,居然会有那么多的人(包括很多共产党员),心甘情愿地拜倒在唯心史观人性论的脚下。难怪毛主席感叹:“我党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的不多”。可见普及唯物史观是多么的必要。
为啥唯心史观人性论具有那么大的号召力?这与人们的价值观或许有些缘份。一旦崇尚富人成为主流的价值观,那么比起土里土气的阶级性,抽象且高大上的人性论从此就具有了温情脉脉的亲和力。
人性成了绅士淑女的通行证,阶级性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墓志铭。
于是乎,使劲挥舞着超阶级的人道主义荧光棒,自觉地跟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撇清关系,就成为绅士淑女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
刘家成先生的“回归人性”,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案例。
《生万物》在描述抗战时期的剧情中,浓墨重彩地展现了地主女儿宁绣绣教农民孩子和文盲识字。似乎农民阶级的识字,只能仰仗开明人士的文化启蒙。
在旧中国,总会有个别开明人士倡导对文盲进行识字教育。开明人士的“开明人性”,或也值得点赞。但是,用地主女儿免费教育农民识字,来叙述农民阶级的文化启蒙,这就是一个历史笑话。
此话怎讲?
《生万物》从地主女儿的善良“人性”出发来叙述旧中国的扫盲运动,极力回避“阶级性”才是扫盲运动的历史主线,这是对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从阶级关系层面展开制度变革的遮蔽和矮化。
那么真实的历史呢?
先看一组数字。新中国成立前夕,全国5.5亿人口中文盲占比高达80%,农村地区的文盲率更是达到了95%。面对这样的文盲大国,从1949年到1964年,中国共产党在军队、农村和工厂中,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四次全国性的扫盲运动。
即便是《生万物》描写的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,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在以陕甘宁为核心的革命根据地,有组织地开展了民众的扫盲运动。著名作曲家马可在延安时期创作的秧歌剧《夫妻识字》,就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。
或问:那么《生万物》描写的抗战时期的山东呢?
回答:即便是《生万物》描写的抗战时期的山东,八路军也在根据地的广大农村大力举办“识字班”,开展了农民的扫盲运动。
实事求是地讲,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,没有劳动人民的阶级觉醒,就不会有从制度层面撼动旧中国的扫盲运动,就不会有农民阶级的文化启蒙。
这才是真实的历史。
刘家成先生说:“我深知,主题的深刻性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关键。”[注4]
很遗憾,如果连撼动旧中国统治根基的扫盲运动都选择性失明,那么所谓“主题的深刻性”,就未免言过其实了。
100多年前,“乞讨兴学”的武训被光绪帝封为“义学正”、赏穿黄马褂,可是大清治下的农民阶级依然是不识字的阶级。电影《武训传》居然把武训塑造为农民阶级扫盲的人性标杆,这不就是一个历史笑话么?
《生万物》对陕甘宁边区开展的扫盲运动视若无睹,对八路军在山东广大农村大力举办“识字班”视若无睹,却大书特书地主女儿的扫盲善举。说委婉一点,这是一个历史笑话;说直白一点,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。
欲知后事如何,且看下集分解。
【注释】
[注1、2、4]刘家成《令人耳目一新的关键(创作谈)——电视剧《生万物》的创作理念》,《人民网》2025年8月25日。
[注3]赵磊《毛刘的差距为啥这么大》,载《昆仑策研究院》。
(作者系西南财经⼤学经济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;来源:昆仑策网【原创】,作者授权首发,修订发布;图片来自网络,侵删)


 红歌会网 SZHGH.COM
红歌会网 SZHGH.COM


